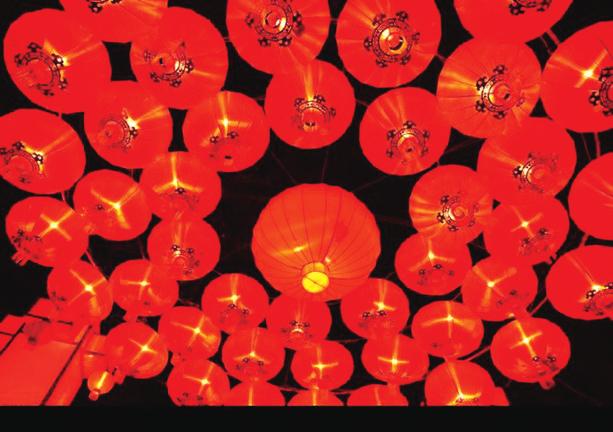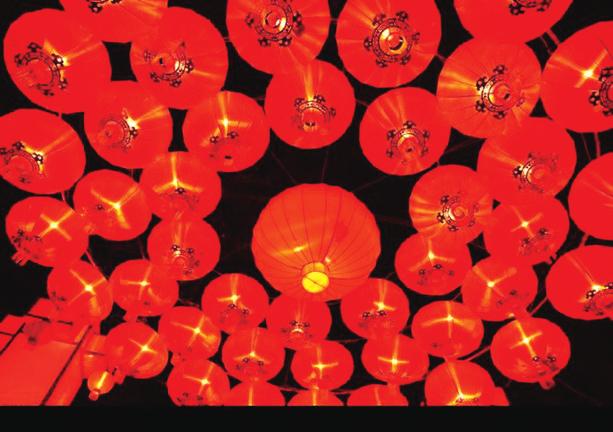
钮士超
父亲是穷人家的孩子,从小没读过书,落下了不识字的底子。
我读小学一年级时,父亲在外打工,每年只有过年才会赶着日子回家,家里一定要提前买好返程的火车票,这是我家年年要记着的大事。每年腊八前后几天,母亲把晒的几根香肠剪掉两根,我跟着她拎了送到房东家里:“他爸要回来嘛,您动动笔写个纸给记一下。”待父亲打长途电话到房东家,让我妈提前买好年后返程的车票:“明个先将回来的火车票打好,正月十五十六都管。”然后就是我听不懂的地名和车次。房东一句句记下来,写成一张纸,撕下来给我妈包在手帕里,买票时就把纸条和钱都给售票员,有座位是好的,没座位能买到车票也是万幸的。
我上初一时,在我妈看来我已是家里的文化人了,家里条件好了些,也装了电话,买票的重任就落在我身上。待到那天一早,我从城南骑自行车到城北的火车票代售点,发现那里早已拥了一堆人了,没人排队,就是凭本事挤。我人小,蹲着钻几下就到了前面几排,直到再也挤不进为止。不管怎么挤,钱一定要紧攥在手,等移到窗口前,手心满是汗,钱都湿了。那时能买到票真是开心,既有买到票的开心,又有能帮家里做事的开心,还有见到父亲的开心,汗湿的纸钱,就是我最早的春运记忆。
到可以网络购票的时候,真是高级了很多。第一次在网上给父亲买回家的票,还是翻出户口本才找到父亲的身份证号。好在那时网上买票的人还不多,插上网银U盾,到了放票的时候,刷新页面果真就买到了,还是有座的。确认了好几遍,就赶紧打电话给父亲说去车站取票,母亲在旁边盯着屏幕也搞不明白:“真买到了吗?别叫人把车票钱给骗走了哇。”下午,父亲打电话回来说已拿到票了,还跟我说他是怎么把身份证给售票员的,人家把票给他,也没再问他要钱,很好很方便。他一句一句说着,我就一句一句应着,父亲又说:“我给你娘俩带了板鸭和栗子。”母亲听到就埋怨:“难吃得很,我不吃,你带回来给你儿吃吧!”从那以后,父亲往返的车票都是我负责。
我成了铁路上的人后,父亲很高兴,说:“好!里子有了,面子也有了!”我笑了半天,实在不知他是收音机里听来的还是自己想出来这么有意思的句子。我就说:“嗯!底子有了,顶子也有了。”二伯在旁边说:“那以后买票方便了!可管带人坐车?”父亲听了欲言又止,看着我“啊”了半天才说:“你那不管买票吧?”我说:“不卖票,我们就管车上,可我跑的车不走你那边。”父亲如释重负,既像是对二伯说,又像是自言自语:“对对,他的车不走这边过,带不了人。”后来我才明白,父亲既想让别人知道我在外面的工作很体面,又怕亲戚来麻烦我。
晚上,父亲到我房间和我聊了几句,然后故作漫不经心地说:“你别有啥负担,工作勤快点,好好干,别让人家觉得你事情多,给同事添麻烦。”我说:“我跑的车真不走你那边过。”父亲笑着放心地回了房。
这便是我和父亲的春运记忆。